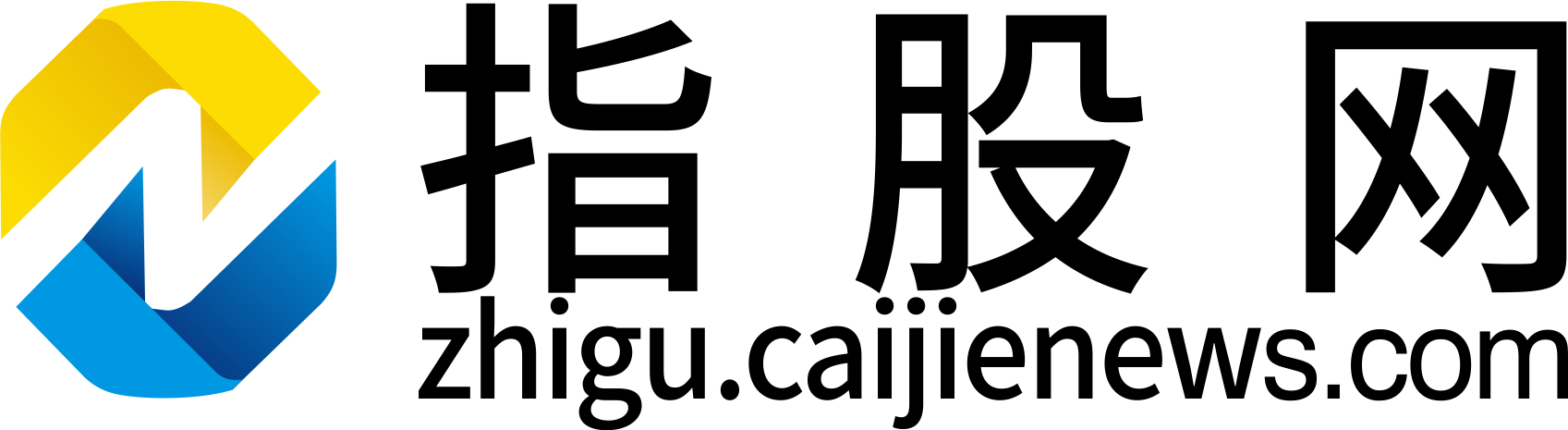
 【资料图】
【资料图】
又到开学季,空气里仿佛弥漫着年轻的气息。当一个教师重新做回学生,会有怎样的体验和感受?在新学期的开端,我们看看小学教师孔晓岩在鲁迅文学院学习的行思感悟。
——编者 剪影重新做回学生,是忐忑而快乐的。 王蒙先生在“春天里的一堂课”中说,苦难未必是坏事。我想,它也许就是磨刀石,人在磨砺中更加强韧,积累了成长的资本。每个人的经历都是各种各样的,能接受美好,亦能接受晦暗,才可悟出活着的意义。 王蒙先生已至耄耋之年,他坐在台上和我们说话,吐字清晰而沉稳,声音有点儿嘶哑。我们静静听他说着:生活本身的格局、历练,值得我们去爱。 鲁迅文学院的学习时光,还像在昨天。大教室窗前垂下的红色帘布,裹着厚重的文明。每一位老师的课堂都给我留下思考,这是我学习的道路上最为珍贵的一部分。 伟大的作品是要有“人”的。这里的“人”,是指将琐碎的个人生活置于家国情怀中,摒弃小我,以宏大的宇宙观,去反映民族变迁的大叙事、大历史。像《人世间》《平凡的世界》等,无不反映了大时代背景之下艰难曲折的历程,这样的作品才能大浪淘沙流传下来。 我们的课堂是多元的,涉及文化与文明、艺术与诗歌、小说与电影、美学与散文、文学与生活、科幻与考古……每一课都颠覆了我的认知,我像一个始终处在饥饿状态的人,想要不停地去充盈自己。 实与虚的问题,是个千古之问。作家刘庆邦老师在“小说创作的实与虚”一课中,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,他道出了虚实结合的三重境界:一、看山不是山,看水不是水;二、看山是山,看水是水;三、山罩一片云,水隔一层雾。他告诉我们,借助“实”,才能到达“虚”的境界,让我们意识到虚写的重要性,既要写出形而上的,又要写出形而下的东西,在有形中做到无形。我的小说写作经验较少,从这一堂课起,我对小说体裁的写作有了新的看法和兴趣。 玉兰2023年3月19日我来鲁院报到,一进大门,先看到的是成片的玉兰花。那天天气很好,金色的光芒洒在这些裹着纯白、粉紫衣衫的花朵身上,我从树下走过,看一场盛大的戏剧从容上演。 寒意未尽,凉风四起,这云海雪涛绚烂的花事令人沉醉。向上望过去,水洗的天上浮云朵朵,玉兰的白有玉的质感,与空远的蓝色融合,浓淡相宜。静观花草的精神妙趣横生,似一幅水墨画,有灵魂,有呼吸,有气韵。今人爱玉兰,近现代绘画大师齐白石画《玉兰》,李苦禅画《玉兰八哥》;古人爱玉兰,五代十国徐熙画《玉堂富贵图》,明代沈周画《写生册·玉兰》,清代余穉画《花鸟图册·玉兰》,清末吴昌硕画《玉兰临风图》…… 学习的日子里,我常常在那儿散步,有时迎着落花。花瓣落在我肩头,像是顽皮的孩子,倏地又不见了,待我寻去,一地零散的花瓣,谁知哪一个是之前的呢?几个女同学从花间小路里走来,像一朵朵玉兰开在春光里。 告别的时候,满枝的绿在热气腾腾的湖水中摇曳着,同学们合影留念,三五成群在鲁院的各处角落。6月的天蓝得似要滴下水珠来,兴许有一滴就落在了离别的眼眶里。 毕业典礼结束后,一位好友得马上赶往机场,我送她到学校门口。她的行李箱小巧却沉重,上车后她与我挥手。我望着车子缓缓离开,隐隐看到一朵花在转瞬的窗玻璃上开出玉兰的模样。 猫 在鲁院散步的时候,常常有好几只猫在树丛中穿梭来去,有白的,有黑的,还有花色的……碰到人,先急促地跑开几步,又停下回过头看着你,喵喵几声,待你蹲下唤它,它又赶紧跑开了。在试探和迟疑中,很少会有真正的信任,心里总设着防呢,除非是它跟了很久的熟人。 它们中最大个儿的是只黑猫,身上带点儿花纹,养得胖胖的,总是在大门口躺着。我们推门进来,怕惊着它,就小心翼翼地走过去,谁想它大模大样地看着我们,仿佛我们的蹑手蹑脚带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 另一只白猫,就不一样了。每次我们和它招手,亲切地唤它,它总睁大一双眼睛喵喵不停叫着。再靠前,它就往后缩一点儿,最后逃离现场,像一团雪球消失在夜色中。但有趣的是,它有时候会躲在高墙拐角处偷偷看着你,同学抓拍过一张照片给我看。那样子像极了近现代画家刘奎龄笔下的猫,狡黠的眼神中似乎透着一丝天真,就这么定定地盯着你,许久都不挪移,它的好奇缩短了猫与人的距离。 日本版画家斋藤清笔下的猫,是诙谐带有浪漫色彩、以漫画形式呈现的,有一幅画我印象很深:宝蓝的底子上,一黑一白两只猫依偎一起,昂着脑袋望着天空,那骄傲的神态俨然上世纪的爵士,简洁的线条,勾勒出猫的高贵中洋溢的孩子气。鲁院的黑猫白猫也曾有过类似的镜头,不同的是,它们垂下脑袋,专注地看着池子里的小鱼。 毕业离校,我是最后一个走出鲁院大门的学生,在我轻轻关上大门的时候,有两个小小的身影目送我。 石头出了大厅走下台阶,左边有个大池子,池子里清亮的水在阳光月光下,都显得那么特别。天气好的时候,水里的颜色有绿有蓝,微波荡漾泛起金光,澄澈动人。楼房的倒影在水里等着各色的鱼儿环绕过去,人若来了,哪怕是极轻的动作,它们也会十分警觉,受到惊吓一样四散离去。等人坐下来不动时,它们又游过来悄悄打探。 月下的水,微微泛着涟漪。水里的月亮偶尔晃动几下,看不见鱼儿,我在水池边的石头上坐下来。从3月到6月,我享受着石头从冰冷到温热的变化,读着上面的文字。石头上本没有字,你若看久了,也会显出字来。无字,甚至比有字更能解放你的思想。 中国人喜欢石头,赏石的传统,自唐宋开始。质朴的石头孕育着独特的文化,人们追求返璞归真的想法也逐渐显现。蒲松龄故居有一块淄博纹石,相貌看起来丑陋,但这种不经雕琢的天然反而让人觉得踏实,“丑陋”的表象之下,才是赏石的美学精髓,就是要“丑”一些,这才抵达了枯寂的境界。明代书法家米万钟爱石头,宋代书法家米芾也是个石头迷,很多时候,他把爱石藏于袖中,不时拿出来把玩。 石头一“丑”,自然就“怪”,如此一来,价值无限。北京保利拍卖会上,一块清代灵璧石以一千多万元的价格成交。黝黑发亮的石身,流经岁月沧桑的洗礼,越发有墨玉的油润,天然的镂空凸显出独特的造型,令人感叹自然造物之绝妙。 鲁院里的拴马桩是让我感觉最神秘的领地,若待上许久,会让我没由来地生出敬畏。这些来自陕西关中一带的石雕艺术品,显得霸气庄严。饱经风雨的剥蚀,那朴拙粗糙的意味在斑驳磨损的石柱上愈加沉稳。狮子、猴子各种雕刻的石像在夕光中,不可侵犯的模样更增添了它们的神圣,每一个表情都是一个凝重的历史画面。 我喜欢抚摸它们苍凉的脊背,在与之目光对视的那一刻,总是心头一惊。 草丛里,几块小石头聚在一处,我弯身捡起,它们的温度和我手心的温度达成某种契合。不问何故同在此,匆匆别后,奔向不同的去处,谁知来日他乡,可会有山高水远的重逢呢? (作者系安徽省砀山县砀城第一小学语文教师、鲁迅文学院第43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)